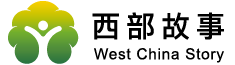回了家,那是临晌午了。奶奶手里倒提着笤帚,嘴里不干不净的叫嚷:“滚!小野货!跟你妈一个样!死去哪儿了?这么些活儿撂给我一把老骨头?你还学会撂蹶子了!嗯?你住这儿本就多了张嘴,我们养着你,你倒嫌福气?皮厚肉痒了不是?”玉娟把头埋进了怀里,她闻到了包子温暖的香味,坚强的她还是没咽住泪,泪眼潸然……

一路小跑着去了厨房(也是卧房和客房)。她跟原来一样的在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搁了粥,还剁了点儿昨天采了来的看着新鲜点儿的马齿苋。又拿出小小的菜碟儿,把两个还温着的包子搁上去,接着把沉甸甸的炕桌抬上高高的土炕,再把临近中午的“早饭”放在这破旧不堪却很干净的小方炕桌上,她微微抬起深埋的头,压着嗓子喊:“爷爷,奶奶,吃早饭了!”奶奶火气未消,上了炕就朝玉娟头上狠狠的几巴掌,玉娟稳稳地忍着,没吱声儿。“野货!滚!做活儿去,别杵在这儿,看了心里就堵得慌!出去!”奶奶喝令,玉娟一两步挪出了房子,去山坳里痛哭。

但玉娟心里还是欣然的。毕竟,以后这阴雨天的的伙食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至少不用绞尽脑汁的去想该怎么准备明日的早饭。这样,玉娟便匆匆跑回家去取房背后的背篓,她可能是化悲愤为力量了吧——手底下利索极了——她在摘野菜。
别过头,她缓了一小会儿。心里想:我怎么能不理解爷爷奶奶呢?谁叫我是个女孩子?唉,我要是个男孩……她又开始了对自己的埋怨。十二年来,能懂事儿的年月几乎时刻都难以忘记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种种遗憾,她的身上仿佛日夜都披着一件浸满雨水的蓑衣,那么沉重,那样阴晦。

她曾经慨叹自己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思想不被自己左右的村落,但凡是女孩,就无休止的被奚落,被嘲笑。但一切无力回天,冥冥之中注定所有,谁都不能抗争,只能妥协。从未认真的看过自己的父母,他们就这么匆匆离开,是如何舍得的?
她不敢多想,怕泪雨滂沱,一发不可收拾。摘了满把野菜,她就忘了奶奶的琐碎,信步走进院里,准备取钱再多买些白面馍,就着雨淋的鲜野菜今儿晚跟爷爷奶奶吃。她得先给爷爷奶奶说声,然后再去县城。心里多得泛滥的悲伤早已成河,她已溃不成军,千疮百孔……她的心里眼里满是县城孩子背着书包去读书的样子,而她只能在这个村落沿袭历史,夜以继日的留守。她也是个烂漫的孩子,她也该有欣悦的童年,可却如此酸辛!

回了家,那是临晌午了。奶奶手里倒提着笤帚,嘴里不干不净的叫嚷:“滚!小野货!跟你妈一个样!死去哪儿了?这么些活儿撂给我一把老骨头?你还学会撂蹶子了!嗯?你住这儿本就多了张嘴,我们养着你,你倒嫌福气?皮厚肉痒了不是?”玉娟把头埋进了怀里,她闻到了包子温暖的香味,坚强的她还是没咽住泪,泪眼潸然……

一路小跑着去了厨房(也是卧房和客房)。她跟原来一样的在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搁了粥,还剁了点儿昨天采了来的看着新鲜点儿的马齿苋。又拿出小小的菜碟儿,把两个还温着的包子搁上去,接着把沉甸甸的炕桌抬上高高的土炕,再把临近中午的“早饭”放在这破旧不堪却很干净的小方炕桌上,她微微抬起深埋的头,压着嗓子喊:“爷爷,奶奶,吃早饭了!”奶奶火气未消,上了炕就朝玉娟头上狠狠的几巴掌,玉娟稳稳地忍着,没吱声儿。“野货!滚!做活儿去,别杵在这儿,看了心里就堵得慌!出去!”奶奶喝令,玉娟一两步挪出了房子,去山坳里痛哭。

但玉娟心里还是欣然的。毕竟,以后这阴雨天的的伙食已经有了妥善的解决,至少不用绞尽脑汁的去想该怎么准备明日的早饭。这样,玉娟便匆匆跑回家去取房背后的背篓,她可能是化悲愤为力量了吧——手底下利索极了——她在摘野菜。
别过头,她缓了一小会儿。心里想:我怎么能不理解爷爷奶奶呢?谁叫我是个女孩子?唉,我要是个男孩……她又开始了对自己的埋怨。十二年来,能懂事儿的年月几乎时刻都难以忘记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种种遗憾,她的身上仿佛日夜都披着一件浸满雨水的蓑衣,那么沉重,那样阴晦。

她曾经慨叹自己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思想不被自己左右的村落,但凡是女孩,就无休止的被奚落,被嘲笑。但一切无力回天,冥冥之中注定所有,谁都不能抗争,只能妥协。从未认真的看过自己的父母,他们就这么匆匆离开,是如何舍得的?
她不敢多想,怕泪雨滂沱,一发不可收拾。摘了满把野菜,她就忘了奶奶的琐碎,信步走进院里,准备取钱再多买些白面馍,就着雨淋的鲜野菜今儿晚跟爷爷奶奶吃。她得先给爷爷奶奶说声,然后再去县城。心里多得泛滥的悲伤早已成河,她已溃不成军,千疮百孔……她的心里眼里满是县城孩子背着书包去读书的样子,而她只能在这个村落沿袭历史,夜以继日的留守。她也是个烂漫的孩子,她也该有欣悦的童年,可却如此酸辛!
421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