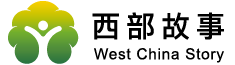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一个女娃哟!唉……”冗长的叹息从一户农家小院里携着厚厚的埋怨渗透进并震颤着我的耳膜。她叫玉娟。一个在遗憾中出生,在呵责里长大的女孩。
乡里乡亲见她就皱着眉嘴里嚷嚷“扫把娟又来了,真个野货!”那是乡亲们以为玉娟的父母是被她克死的。其实,在玉娟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爷爷奶奶觉得儿子媳妇不孝,当他们过事儿了,乡亲们也便十里八乡的说玉娟是“没娘娃儿”、“扫把娟”。爷爷奶奶确实是玉娟的亲爷爷奶奶,可他们怎么也这么憎恶玉娟儿呢?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在那山坳里的小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此时的玉娟,无论是经济的一贫如洗还是精神的溃不成军都让她心力交瘁,可乐观的她总能够怀揣着信念好好儿的活下去。

半夜四点半,玉娟就得按着点儿起来。她得生火,烧开水,做早饭……那烧火的干柴草是前天晚上九点多在山坳里枯树枝杈上折的,背篓里头搁得满满的才能回家里。每天早上,烧水就得两个多小时,家里大瓶小罐全都要灌的满满的,这不是一件清闲的等开水开开就行的差事,煮开水得闲当儿,还得算好时间段儿再跑去山坳里找苦苦菜或者苜蓿,这都是暮春长的野菜,其他的季节还得去找别的能吃的东西。幸亏这正是苦苦菜和苜蓿长得最茂的时候。随便采了来,早饭便够了。
今年种的春麦收成不错,农社发下的补贴也能够使,玉娟心里知足。自家春麦磨得面有点儿边角是搁在家里搪瓷面缸里用来下面,做拌汤或者做饽饽的。还有些是农闲时候玉娟自己去县城拾掇破烂儿挣得些零钱买的并不多贵的粗面。

早饭简单极了,似乎每天都那样儿——自家春麦磨的面和自己拿碎钱买的粗面和着搁到开水锅里头,边搅边熬,不敢多放,怕的是一个月下来那些面不够,又被爷爷奶奶狠狠的数落,狠狠的责打。所谓的拌汤,也便是开水里搁了小半把混合面儿。怕这汤水太寡淡,玉娟便把摘来的苦苦菜切碎碎的,往汤面上一撒,也算是有了点绿气儿。接着玉娟就细心地盛到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并把两个老人叫起来吃早饭。他们总是停不下对玉娟种种不满的说道,玉娟也不会不耐烦,十二年,别的功夫且说怎么样,但这个“忍”字儿,玉娟练出来了。

晴天倒好,只晒晒,皮糙的玉娟也不怯着酷热难耐。反而这阴雨天让玉娟死一回样儿的头疼、心烦。这天气还真不心疼这可怜的姑娘,偏偏在今年的秋后,雨连绵不绝,哭丧似的天整日淅沥,搅得玉娟无所适从。
阴雨连绵,枯树上的枝杈都被浸透了,潮腾腾的,拿什么生火呢?屋子里多余下的也都眼巴巴的瞅着用尽了,打五岁开始主事家里的大小杂活儿起,还没遇见这么闹心的事儿。不能生火,这水没法烧,饭别提该怎么做。似乎几场阴雨绝了玉娟和爷爷奶奶的口,肚子填不饱,哪有气力做事儿呢?看着竹篓里还盛着几个饽饽,那是上次做的时候面攘多了,吃剩的几个,这余的几天,还能给爷爷奶奶填饱。于是,玉娟每早仍旧四点半起来。把那几个快放酸的冷冰冰的硬饽饽捂到怀里,就这么捂着,捂着……两个多小时过了,饽饽也和玉娟的体温也将近了,她原照着以前的样儿,在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各放一个软和了的饽饽。而她自己就去阴冷的山坳里吃凉到心里的枯黄的叶菜。她知足,她至少没有饿肚子,这小小的山坳给了她多少温暖啊!她怎能不知足呢?她的世界顿时温馨起来,她觉得一切真的没那么糟,她相信自己可以挺过去。

“一个女娃哟!唉……”冗长的叹息从一户农家小院里携着厚厚的埋怨渗透进并震颤着我的耳膜。她叫玉娟。一个在遗憾中出生,在呵责里长大的女孩。
乡里乡亲见她就皱着眉嘴里嚷嚷“扫把娟又来了,真个野货!”那是乡亲们以为玉娟的父母是被她克死的。其实,在玉娟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爷爷奶奶觉得儿子媳妇不孝,当他们过事儿了,乡亲们也便十里八乡的说玉娟是“没娘娃儿”、“扫把娟”。爷爷奶奶确实是玉娟的亲爷爷奶奶,可他们怎么也这么憎恶玉娟儿呢?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在那山坳里的小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此时的玉娟,无论是经济的一贫如洗还是精神的溃不成军都让她心力交瘁,可乐观的她总能够怀揣着信念好好儿的活下去。

半夜四点半,玉娟就得按着点儿起来。她得生火,烧开水,做早饭……那烧火的干柴草是前天晚上九点多在山坳里枯树枝杈上折的,背篓里头搁得满满的才能回家里。每天早上,烧水就得两个多小时,家里大瓶小罐全都要灌的满满的,这不是一件清闲的等开水开开就行的差事,煮开水得闲当儿,还得算好时间段儿再跑去山坳里找苦苦菜或者苜蓿,这都是暮春长的野菜,其他的季节还得去找别的能吃的东西。幸亏这正是苦苦菜和苜蓿长得最茂的时候。随便采了来,早饭便够了。
今年种的春麦收成不错,农社发下的补贴也能够使,玉娟心里知足。自家春麦磨得面有点儿边角是搁在家里搪瓷面缸里用来下面,做拌汤或者做饽饽的。还有些是农闲时候玉娟自己去县城拾掇破烂儿挣得些零钱买的并不多贵的粗面。

早饭简单极了,似乎每天都那样儿——自家春麦磨的面和自己拿碎钱买的粗面和着搁到开水锅里头,边搅边熬,不敢多放,怕的是一个月下来那些面不够,又被爷爷奶奶狠狠的数落,狠狠的责打。所谓的拌汤,也便是开水里搁了小半把混合面儿。怕这汤水太寡淡,玉娟便把摘来的苦苦菜切碎碎的,往汤面上一撒,也算是有了点绿气儿。接着玉娟就细心地盛到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并把两个老人叫起来吃早饭。他们总是停不下对玉娟种种不满的说道,玉娟也不会不耐烦,十二年,别的功夫且说怎么样,但这个“忍”字儿,玉娟练出来了。

晴天倒好,只晒晒,皮糙的玉娟也不怯着酷热难耐。反而这阴雨天让玉娟死一回样儿的头疼、心烦。这天气还真不心疼这可怜的姑娘,偏偏在今年的秋后,雨连绵不绝,哭丧似的天整日淅沥,搅得玉娟无所适从。
阴雨连绵,枯树上的枝杈都被浸透了,潮腾腾的,拿什么生火呢?屋子里多余下的也都眼巴巴的瞅着用尽了,打五岁开始主事家里的大小杂活儿起,还没遇见这么闹心的事儿。不能生火,这水没法烧,饭别提该怎么做。似乎几场阴雨绝了玉娟和爷爷奶奶的口,肚子填不饱,哪有气力做事儿呢?看着竹篓里还盛着几个饽饽,那是上次做的时候面攘多了,吃剩的几个,这余的几天,还能给爷爷奶奶填饱。于是,玉娟每早仍旧四点半起来。把那几个快放酸的冷冰冰的硬饽饽捂到怀里,就这么捂着,捂着……两个多小时过了,饽饽也和玉娟的体温也将近了,她原照着以前的样儿,在爷爷奶奶各自的搪瓷碗里各放一个软和了的饽饽。而她自己就去阴冷的山坳里吃凉到心里的枯黄的叶菜。她知足,她至少没有饿肚子,这小小的山坳给了她多少温暖啊!她怎能不知足呢?她的世界顿时温馨起来,她觉得一切真的没那么糟,她相信自己可以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