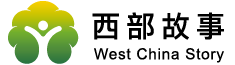彪子不愧是班里的花儿王子,声音虽然还有一些稚气,但对花儿的韵调、节奏、情感都把握的非常准确,略带磁性的声音让米军感到振奋。在花儿的陪伴中他们迈开步子向另一座山梁走去。一路柳树飞快地前来迎接他俩,不觉间已翻过山梁穿过山谷。路一拐弯,学校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赫然映入眼帘。那生锈的铁皮大门完全敞开,校园里早到的同学三三两两在墙角聊天。彪子走过去笑着和他们打招呼。米军则径直朝操场边上的那排高大笔直的有一抱子粗的白杨树走去。整齐的白杨树依旧挺拔,它们的一律向上的落光叶子的枝桠紧紧靠拢着,直插向云霄里去了。光滑的淡青色的肌肤无法遮掩他们体内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它们从未放弃过任何成长的机会,倔强地努力地生长着,仿佛寒冻的风霜只不过是它们笑对生活的催化剂一般。
米军的目光集中在第七棵杨树上,久久没有移动。这是他上一年级时亲手栽的,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年年树相似,岁岁人不同,每一次听风雨敲打树叶,仿佛一个声音低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六年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85年4月13日,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阳光穿过树枝照在那些为迎接春天而绽开的花朵上,七岁的小米军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将会发生什么。天是那么蓝,一丝云也没有,空气清新的就像用水洗过一样,也许生活就像罂粟花,耀眼夺目的外表背后往往就隐藏着寸断肝肠的旷世奇毒。
那天学校按排植树,米军用铁楸挖好坑,选了一棵笔直的小树苗栽了进去,培好土,浇了半桶井水。栽好后,米军用小刀轻轻地刻上自己的名字,并暗暗地记住从东往西数是第七棵。也许是劳累的缘故吧,劳动完毕,米军感到浑身无力,回到家里,就倒在炕上睡着了。谁又曾想到,就是那天,他突然发高烧,家里人一开始还以为感冒,到村里的赤脚医生那里买了药给他吃。10天后,米军的高烧还未缓解,父亲才送他去县医院。医生诊断后遗憾地说:米军得的是小儿麻痹症,因为这种病的潜伏期症状不明显,结果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期,他的这一辈子恐怕得靠拐杖走路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父亲捶胸顿足懊悔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冷酷的现实打破他们急切在脑海里构想出的一千个治好儿子病的方案后,一向憨厚内敛的父母在医院的楼道里号啕大哭。
米军后来才知道,那天,父亲是流着泪跪在医生的面前,求医生无论如何也要救救他的孩子。米军可以想象到,一个父亲,听到这样一个霹雷般的厄运降临到他不足7岁的孩子身上,是如何的痛不欲生。他仿佛看见泪如泉涌的父亲的脸埋在身体内抽搐的身影。仿佛听到母亲在医院空荡冰冷的水泥楼道里那撕心裂肺般被冲撞碰碎的哭声和泪水滂沱而下的渗入地平声音。但不论是父亲的悲痛还是母亲的眼泪,都无法改变既定的事实,米军最终右肢瘫痪萎缩,不得不依靠僵硬的拐棍生活了。几天后,米军从父母的眼神里和日渐麻木的右腿中,看出了自己命运。才步入生活轨道的少年突然从树阴森森的枝头被飞弹打中,跌落在黑暗的无底深渊。风云突变,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天空乌云迷布。一个刚刚才绽开的花朵,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落在污浊的泥泞中,一轮刚刚升起的太阳,被狂风卷起的漫天乌云所遮蔽,米军觉得世界顿时黑暗无比。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悲伤,愤怒,苦恼,连续几个星期,米军把自己的心紧紧的封闭起来,一个人躲在病房的角落里,任凭谁劝他都不说一句话。此时他觉得那个寂静而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有温情和怜悯。他也不需要同情和怜悯,他就像无鳍的鱼溺水,被汹涌的悲痛所吞没。爱不再是无云的天空,也不是雨中的彩虹,更不是温暖的阳光和亲人的爱抚。爱是撒在鲜血淋淋伤口上的咸盐,是根根扎进手指的的竹签,是嗖嗖穿心的万箭,如万只蚂蚁不无时无刻地啃噬着他的心,有时,他仿佛能听到喀嚓喀嚓的虫子啃噬心灵的声音。那段时间,是米军生活中最黑暗最漫长的日子。他像是在海中航行的一条小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海上迷雾重重,他不知道风雨飘摇的小舟该驶向何方……
米军注视杨树的双目紧紧闭起,脸色异常紧张而苍白的几乎失去了血色,呼吸明显有些急促,两道剑眉也拧成了疙瘩,鬓间暴起的青筋不时地抽动着,他的上齿使劲地咬着发紫的下唇,似乎要咬出血来才肯罢休。本来抚摸杨树的温柔的手指此时也颤动着抽痉似的蜷在一起,指甲深深地扣进了树皮里,仿佛正在经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或是挣扎于一场可怕的梦魇之中。猛的,一阵冷风袭来,米军激伶伶打了个冷颤,发觉自己身陷几经努力忘记却又始终无法忘记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时,他苦笑了一下,定了定神,随即摇摇了头,转身向教室走去。
676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