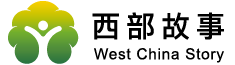妈妈又因胃出血住院了,我去医院看她。病房的门半掩着,我看到了妈妈因连日打点滴而且没吃饭而消瘦的脸,鼻子酸酸的。 我站了一会儿,将飘去远方的思绪拉了回来,轻轻地推开门,叫了一声:"美女!"听到我的声音,妈妈连忙抬起头也说:"嗨,美女!"我和妈妈经常这样打招呼。我问妈妈:"怎么样了?"她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到:"这次比上次好一点,没事儿的,不用担心。"其实这次虽然没有上次严重,但是没有妈妈说的那么好,在门口我就已经看到了她痛苦的表情,但是她每次一看见我和姐姐,总是会用最美的微笑来面对我俩。妈妈听我说着家里的事儿,开着玩笑,斗着嘴,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心……

那晚,我没有回家,在医院陪着妈妈。妈妈打点滴一直到了凌晨3点多,我1点多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又酸又甜的梦。
梦中我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熟悉而且仍在来回的车站;回到了那个可笑而又记忆深刻的走廊和琴房;回到了那个欢乐而又惊心的夜晚……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那个夜晚的梦中回放。
寒风吹拂着,使劲儿地往路人的脸上刮,那时才是早上7点,妈妈.姐姐和我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车站。我们穿着大棉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可尽管这样,那讨厌的寒风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冷。我们要去桥头,我和姐姐所在的舞蹈班被邀请去参加大通的春节联欢晚会,老师让大家7:30在班里集合,大家集体化妆,今天先去彩排。舞蹈班设在县城离我家很远,而且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农村的,每次我和姐姐都要比她们早一个小时起床,然后妈妈领着我俩去上课。梦中的车站上依旧有来来往往,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依旧不认识他们的面容,却认识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认识他们爬满皱纹的额头;认识他们突起的脊背,这些都只是为了父母早已奔波时还窝在舒适的被窝里,做着美梦,想着醒来之后吃什么好的孩子们......春.夏.秋.冬都从未改变过,而妈妈.姐姐和我就是他们的见证者,我们记住了他们疲惫或沮丧的身影,记住了他们高兴或失望的面容......

妈妈又因胃出血住院了,我去医院看她。病房的门半掩着,我看到了妈妈因连日打点滴而且没吃饭而消瘦的脸,鼻子酸酸的。 我站了一会儿,将飘去远方的思绪拉了回来,轻轻地推开门,叫了一声:"美女!"听到我的声音,妈妈连忙抬起头也说:"嗨,美女!"我和妈妈经常这样打招呼。我问妈妈:"怎么样了?"她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到:"这次比上次好一点,没事儿的,不用担心。"其实这次虽然没有上次严重,但是没有妈妈说的那么好,在门口我就已经看到了她痛苦的表情,但是她每次一看见我和姐姐,总是会用最美的微笑来面对我俩。妈妈听我说着家里的事儿,开着玩笑,斗着嘴,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心……

妈妈是一名幼儿教师,一个月只有600块工资,那时妈妈在读幼师,我和姐姐上完课之后就去妈妈学习的地方,等妈妈上完课,我们就一起回家。那时我家家境有些拮据,中午我们自己带着馍馍。妈妈的教室在四楼,每层楼道的转弯处都有个水龙头,我们的中午饭就是馍馍和自来水。中午下课了,人们往外走,我们等到人都走光了,才轮流去打水。等到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在楼道里唱歌跳舞,完全不顾过路的人投来的好奇的目光,我们只顾自己开心,快乐。

每次这天下午妈妈都回去琴房练琴,我先是从门缝里偷偷的听课,等到老师讲完课,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溜进去坐在他留意不到的地方,在琴上比划自己偷学到的。总没有那么幸运,终究还是被老师逮到了,那时我正陶醉在自己的琴声中。"这是谁的小孩儿啊,怎么带到琴房里来了?"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然后就看见妈妈笑着跟老师求情,求他别把我赶出去,只听见那个老师说:"放心,这个小家伙挺机灵的,你练你的吧,我教教她。"就这样,我学会了弹琴,有一个免费的老师......
舞蹈快要考级了,老师要求加课,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妈妈下班后先帮我俩收拾跳舞用的东西,等到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去桥头。那是第一节课,下课时已经是8:30了,回家的车已经没了,我们回不了家,又不敢住宾馆,就在大街上晃悠,风儿激情高涨,吹的我们直发抖。实在没办法了,妈妈就领着我和姐姐去了医院,医院的楼道里有给家属坐的凳子。我们上了三楼,三楼正好是骨科,我们的对面正好是抢救室。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凄惨的痛苦声和悲强的哭叫声。虽然妈妈当时尽量地捂着我俩的耳朵,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每次想起来,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梦的结尾以我们欢乐地笑容结尾,我醒了,妈妈早已经起来了。看着妈妈的眼神,好像在忽然之间懂得了什么,我迷茫了......妈妈叫我帮她揉揉肩,看着妈妈眼角爬上来的眼纹,看着妈妈松弛的肌肤,我终于明白了,妈妈老了,我长大了。

那晚,我没有回家,在医院陪着妈妈。妈妈打点滴一直到了凌晨3点多,我1点多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又酸又甜的梦。
梦中我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熟悉而且仍在来回的车站;回到了那个可笑而又记忆深刻的走廊和琴房;回到了那个欢乐而又惊心的夜晚……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那个夜晚的梦中回放。
寒风吹拂着,使劲儿地往路人的脸上刮,那时才是早上7点,妈妈.姐姐和我早早的就已经来到了车站。我们穿着大棉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可尽管这样,那讨厌的寒风还是让我们感到很冷。我们要去桥头,我和姐姐所在的舞蹈班被邀请去参加大通的春节联欢晚会,老师让大家7:30在班里集合,大家集体化妆,今天先去彩排。舞蹈班设在县城离我家很远,而且只有我和姐姐两个农村的,每次我和姐姐都要比她们早一个小时起床,然后妈妈领着我俩去上课。梦中的车站上依旧有来来往往,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依旧不认识他们的面容,却认识他们布满老茧的双手;认识他们爬满皱纹的额头;认识他们突起的脊背,这些都只是为了父母早已奔波时还窝在舒适的被窝里,做着美梦,想着醒来之后吃什么好的孩子们......春.夏.秋.冬都从未改变过,而妈妈.姐姐和我就是他们的见证者,我们记住了他们疲惫或沮丧的身影,记住了他们高兴或失望的面容......

妈妈是一名幼儿教师,一个月只有600块工资,那时妈妈在读幼师,我和姐姐上完课之后就去妈妈学习的地方,等妈妈上完课,我们就一起回家。那时我家家境有些拮据,中午我们自己带着馍馍。妈妈的教室在四楼,每层楼道的转弯处都有个水龙头,我们的中午饭就是馍馍和自来水。中午下课了,人们往外走,我们等到人都走光了,才轮流去打水。等到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在楼道里唱歌跳舞,完全不顾过路的人投来的好奇的目光,我们只顾自己开心,快乐。

每次这天下午妈妈都回去琴房练琴,我先是从门缝里偷偷的听课,等到老师讲完课,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溜进去坐在他留意不到的地方,在琴上比划自己偷学到的。总没有那么幸运,终究还是被老师逮到了,那时我正陶醉在自己的琴声中。"这是谁的小孩儿啊,怎么带到琴房里来了?"我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然后就看见妈妈笑着跟老师求情,求他别把我赶出去,只听见那个老师说:"放心,这个小家伙挺机灵的,你练你的吧,我教教她。"就这样,我学会了弹琴,有一个免费的老师......
舞蹈快要考级了,老师要求加课,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妈妈下班后先帮我俩收拾跳舞用的东西,等到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去桥头。那是第一节课,下课时已经是8:30了,回家的车已经没了,我们回不了家,又不敢住宾馆,就在大街上晃悠,风儿激情高涨,吹的我们直发抖。实在没办法了,妈妈就领着我和姐姐去了医院,医院的楼道里有给家属坐的凳子。我们上了三楼,三楼正好是骨科,我们的对面正好是抢救室。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凄惨的痛苦声和悲强的哭叫声。虽然妈妈当时尽量地捂着我俩的耳朵,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的,每次想起来,都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梦的结尾以我们欢乐地笑容结尾,我醒了,妈妈早已经起来了。看着妈妈的眼神,好像在忽然之间懂得了什么,我迷茫了......妈妈叫我帮她揉揉肩,看着妈妈眼角爬上来的眼纹,看着妈妈松弛的肌肤,我终于明白了,妈妈老了,我长大了。
610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