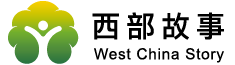在四川山区深处,寥寥炊烟升起的时候,背着竹背篓,佝偻着背,穿着破烂不堪的粗麻布衣的篾匠,在崎岖不平地泥巴路上踩出了一个又一个深浅不一的脚印,哼着小曲儿开始走村窜户的找活路。
八十年代的山村,如果哪家有一副蒸笼之类的竹制品的话,那就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大户人家了。一年冬天,我哭闹着想吃馒头,于是紧紧拽着母亲的手,眼泪汪汪地盯着她,最终母亲也已无可奈何而告终,只有去向邻家借蒸笼,可借的次数多了,脸皮也开始变薄了。上个月,父亲一咬牙:"请蔑匠来扎一副。"

记忆中的蒸笼
我们家熟识的篾匠是个哑篾匠,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曾听我父亲说起过,他小的时候好像得了一场大病,导致他说不出话,后来又因为家庭所迫,只好外出学艺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多年来的劳累也使他的双腿出现了问题,可幸的是,他练就了一手好手艺。
初冬的阳光刚跃出山头,一抹暖阳跟随他进了我家院子,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蹒跚走了过来。老人形容枯槁,蓬头垢面,背上背着背篓,背篓里还杂七杂八的放了一些类似于工具之类的东西。他的背在夕阳的映衬下微微的有些驼。当他和我父亲的目光不经意间撞在一起时,我看见老人深陷的眼窝里涌起了鲜活的内容。他迟疑了一下,停住了脚步,接下来,他一边说着含混不清的话语,一边用手比划和父亲交流。父亲说:"慈竹就在屋后呢。"篾匠从背篓里拿出砍刀,去竹林里选竹子。因为他腿的缘故,父亲不放心,就叫我跟了过去,他砍一根,我扛一根,伴着那一声声"嘿嘿"的笑,竹子也砍的差不多了。

"我"家房屋后面是一片竹林
到了屋前,我们把一根根长而直挺的绿竹放在了圆坝上,母亲也早已煨好了茶,招呼着我们去品尝一下她煨茶的技术。品完后,只见篾匠从他那深不见底的衣包里掏出了一杆叶子烟,含在嘴里开始忙了起来。从锯开始,经过剖、拉、削、磨、刮等工序,一根根竹子变成蒸笼格的竹片,变成了蒸笼盖的篾条,变成了蒸笼的外框……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我发现唯一没变的就是他那一直含在嘴里的叶子烟。
我因生性调皮,所以就故意靠近篾匠的背篓,想瞧一瞧里面都有什么稀奇玩意,他竟像宝贝一样护着他,可是,篾匠不喜欢别人靠近他的背篓,一靠近他就开始"啊啊啊"喊叫,我感到很诧异,便站在他背篓旁,问他:"叫个啥呢,我又不拿你的,真小气"。
我带着遗憾坐在圆坝的阶梯上,迎着初升的朝霞,我掏出了一本小诗开始朗诵了起来,声音传到了篾匠的耳朵里,他转过身来,衔着叶子烟,眯着眼睛,双手不停的拍掌,从他的嘴里还时不时的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和赞许。呜呼,在这种年头能使人谅解而不会以口舌招锅者,唯有真正欲言不能的哑巴耳。夫哑,本是残疾之一,不料竟成为篾匠习焉不察的事。
一切准备妥当后,篾匠从柴堆里抱出了一捆干柴,放在圆坝上,点起了火,在大火还没燃起来前,篾匠便趁此间隙,把背篓里的工具倒了出来一样一样的清点,以防有漏。其中有给抛开的竹子里面拉上口子用的弯刀,有用来锯竹子长短的锯子,还有用来撮竹头的撮子……等到大火燃起来后,篾匠便把准备好的竹片放在火上烤,等竹片烤得滚烫时,篾匠便要趁热拉成圆圈。他先用厚布垫上,一头拉在手上,一头踩在脚下,使劲拉手上的竹片,脚顺势移动,最后把拉过的竹片两头接上,木夹子夹住,再调整几下,竹圈就圆了起来。其中做蒸床是最考验技术的,着床的竹片隙缝小指那么宽,窄了,蒸汽上不来;宽了,气全部跑顶上了,这时,篾匠用手在上面比了比尺寸,用心琢磨了一会儿后,用篾刀砍了一个口子下去,顺着口子剔开一隙缝。这样子,就算大功告成了。另外,在我们家乡,还流传这么一句话:"篾匠学的会,鸡屎食三坨;篾匠学得精,鸡屎食三斤"生动形象地道出了篾匠生涯的艰辛和无奈。

蔑匠开始做蒸笼
四床蒸笼做好了以后,篾匠便用小刀在上面刻了一行小字,刻的是"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敝月……"五分遒劲,五分柔媚,还有十分潇洒开朗。他用手不停地比划着,同时也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我懂了,这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东西,也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有文化的几句话吧!
蒸笼扎好了,那一年过年,我家蒸的馍格外香甜。
夕阳下,他的身影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背篓里的工具碰撞出好听的旋律。
他的身影被余晖拉得很长很长,很直很直……

蒸笼做好了,蔑匠也要走了
958 |
0 |
2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