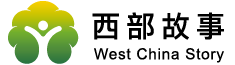我静静地坐在窗前,看着旧木门外的那片茶园,园间是连绵的青色,早雾还未散去,晨露依旧布在上面,闪闪发光。春光无限,旧梦依稀。
这里是我的故乡。
南郑,我的故乡。近日我回到老家,当我走进这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时,我却有些哀伤。茶园里的茶树正茂密地生长着,阳光透过树的缝隙蔓延在我的脸上。这个我儿时的家,仿佛有些冷清。外婆已去了西安,陪着她即将出生的孙子。
只有平日不爱说话的外公还有我敬爱的太公,太婆。他们都已年老。而我正如那茶树,向阳而生。我给外婆打了电话,她正在菜市场买菜,有很多嘈杂的声音,但她还是听清了我说的话,最后她安慰我说,她三月一定回来,给我用石斗蒸面皮,给我泡新发的汉水银梭。我笑着回答了她,然后挂断了电话。
外婆说的用石斗蒸面皮和汉水银梭,都是南郑独有的美食,也是我抹不去的乡愁。
犹记儿时,外婆总是会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从井里挑好水,一步一步地担到石斗前,用清水一遍一遍地冲洗,直到石斗完全干净后,才将洗好的米混着水放在石斗上慢慢研磨。这时的我,会常常坐在她的身边,看着她的模样。一块破烂的花布盖在她的满头黑白混杂的头发上,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漆黑发亮,像是黑夜里的星星。我不禁感叹,原来时间是真的可以磨损人的,自从我上次见她,她已经老的厉害,可是她在我的印象里却是那么年轻和明亮的,我亲爱的外婆。
那时的她还算年轻,手法很是熟练。巨大的石碾把压碎的米变成了浓厚的米浆,流淌在墨青色的石斗里,最末处放一个红色的水桶,接着流下来的乳白色的米浆。想来我儿时的味觉体验,也是由此开始的。
把桶提回去后,外公已经刷洗完了铁锅,摆上了蒸面皮的铁架和布,架好了柴火,只等外婆的米浆。蒸面皮这个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外婆蒸,我外公架火,这是他们多年来的默契。不必言说,却能心领神会。蒸汽一直在铁锅上循环,外婆总是会根据蒸汽判断出锅的时机。第一张我是不吃的,因为太厚,外婆总是给我第二张,第二张的口感软糯柔滑,配上调料,一时间所有的味蕾都会带来香与辣的双重体验。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家乡味道吧。我应是永远都忘却不了。
还有一种记忆是关于茶的。庭前的茶树是外公细心栽培的南郑名茶——汉水银梭。扁平似梭,翠绿批毫;嫩香持久并带花香,汤色浅绿,清澈明亮,滋味鲜出、耐泡回甘;叶底柔嫩、芽头肥壮、黄绿匀亮。
我仍旧记得,在夏夜月光如水的庭院里,外婆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脱下汗湿的衣服,换上干净整齐的新衣。拿出存放很久的茶,把炉子里的水烧至翻滚,然后准备好喝茶的瓷器。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认真仔细。那时的我不知她对茶是如此敬重的,仿佛有一种神圣的仪式。或许,这只是一个背朝天面朝黄土的劳动者对清茶的卑微敬意。这是生的欢喜与希望。
于是,我,外公,外婆一起坐在庭院的石桌上,桌上放着一杯沉年已久的汉水银梭。
汤色澄碧而清冽,气息馥郁而沁芳,数滴入喉,如兰的清香味充满齿颊。小口饮之,回肠荡气,顿觉置身翠绿深处,犹如回归自然,神清目朗。对着月亮,满饮此杯。这时的我忽然想起了小时学的散文——荷塘月色。不过不同的是,荷塘变成了茗园,但月色依旧。直至今时今日,亦别有一番感动。
最美好的季节是在秋季,庭院里的桂花开发,满园的桂花香味。流动的月光在院子里跳着舞,这时的外婆会以桂花酥和银梭茶来犒劳丰收后的我们。那真是沉甸甸的喜悦,是关于我们三个人独特的喜悦,是对于生命的眷念和当时明月的思念。
可惜都回不去了。那时的茗园已变成了旧梦,只是化作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
久久挥之不去。
院里的那棵茶树又发了新芽,但是这时节,终归是没有人来。我很想给远方的外婆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们一切都好,我们等着她回来。
茶园之春
采茶

外公外婆

石磨
635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