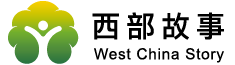好像好久不曾看到花了。
或者,我的心好久没有看到花了。
好多时候,有人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园丁。
还记得十几年前,怀揣梦想,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山村,叫做逊让,好像离开家很远,很想家。那是一个占地不到一亩的校园,一共有六间房,很陈旧,安着小木窗的那种。校园是在崎岖的沟壑边拓展开的,学校正在山脚下,山坡不太高,但很陡,所以即使在夏季,太阳的光辉也显得很珍贵,四点多就捱过了山边,不见了踪迹。校园里有一根锈迹斑斑的国旗杆子,有时候,上面会挂着一面红旗,不过已经褪去了红色,像天边的一抹晚霞。有两位同事,三十来岁的样子,很朴实,和当地的农民并无二致,他们成了我最熟悉的人,有点大哥哥的味道。他们的家都在村子上,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因为是民办老师,家里种着一二十亩地,所以很忙,应该说他们都是好丈夫,好家长,为了生计,皱纹过早地爬上了他们的额头。每月中旬发工资,因为是民办教师,每月可以领到四十块工资,有时候他们也喝点酒,很低档的那种,于是不久,我也学会了喝酒,还有抽烟,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那时候最奢侈的便是吃煮鸡蛋,一口气可以吃七八个,据说吃点东西不容易喝醉,但好多时候还是喝的大醉,几个男人,吆五喝六,唱着最地道的“少年”(青海民歌,花儿),然后,在暮色沉沉中各自散去,留下一村的喧哗和狗吠。在这种日子里,我便很容易的睡去。
那时候有一辆班车和外界沟通,星期日我便早早赶着班车来到学校,打扫卫生,生火做饭,当然,还有备课。趴在素白的,有点土色的桌子上,一直到深夜,然后爬上那面专门为我搭起的土炕上,辗转睡去。可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的早早起来,认真洗漱一遍,满怀激情地上完课,在夕阳将落的时候,哼着变腔走调的流行歌曲,赶着末班车回家去,那个时刻感觉好幸福。
村里的路很难走,下雨天总是一路泥水,因此两个同事常常穿着泥靴来上课,通讯也不方便,曾经用自己上完学打工的钱买了一台收录机,尝试着和外界做一些沟通,可是没有一点属于人类的声音冒出来,只好作罢。想想也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倒是六根清净。全村没有一个电话,因为村子也不大,所以人们的嗓子便发挥了最大的效用,个 个都是嗓音嘹亮,极具风格。好多时候,早起放牛的妇女们在叫孩子起床上学的同时,也将我附带着叫醒了。
有一天,看着校园一片白地,忽然心血来潮,动员学生从家里带点树苗,于是,苦于无聊的我便找到了一点消遣,放学后,一边督促没有完成学习任务的孩子学习,一边便拿着借来的铁锹挖坑栽树,一两个月过去的时候,小学校的围墙边,便立起一圈杨柳的篱笆,心中颇有一些成就感。如今,许多年过去,不知道我植下的小树是否长高了一点。
好多年过去了,往事犹如飘零的花瓣,随风而逝,不知所踪,可是,唯有那青涩的青春记忆,好像寒冬里的塑料玫瑰,愈发鲜艳,满园缤纷的日子已经过去,不经意间,又看见了她。
1698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