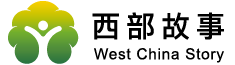她说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就像梦一样,人生几十年仿佛只不过一个秋。
她蹒跚着走过柜子旁,推开那扇已裂开的木框纱门,两只手扶在膝盖上,慢慢的坐在那把老竹椅上,坐下竹椅的那几秒,岁月在吱吱作响。她沧桑的脸在斜阳下朦胧的只剩轮廓,可我却看见了迂回的条条线线爬满了额间眉头,那么分明。
八岁。她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忙活着,熟练地将哥好的猪草放在竹篮,光脚笑着跑回家里,她想着这几天都没能去上课,趁父母出门要好好看书,不能再耽搁了。推开门,是四个比她还小的弟妹嚷着要吃东西。她放下手里的竹篮,长呼出一口气,从院子里所剩不多的萝卜中拔下最不起眼的一根,煮了一锅刚够四个半碗的萝卜汤分给了弟妹,又从枕头下摸出八颗已被放潮的花生分给了弟妹一人两颗。她看着一干二净的碗边零散着的花生壳,把口水往下咽了咽,打开了书。
17岁。她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忙活着,熟练地将一根根秧苗插进了土里,挽起的裤管上满是大地溅起的繁星点点。她听见了远处母亲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唤,忙将手中还未插完的秧苗放下,将头上的汗水往衣服上的补巴处蹭了蹭。抬起头,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热切眼中的欣喜。于是她就像母亲来时那般,揣着好奇与小鹿乱撞的雀跃跑去了村口。她梳着被汗侵湿的油亮亮的大粗辫,穿着泥渍斑斑还挽起的裤子去见了那个比她大了五岁的男大学生。那是一个和她一样清澈的男生。那天,他们一见钟情,眼中满是坚定与纯粹。她望向他深情款款的那一刹那,脸像是被染过的半片绯红。
二十岁,乡里办学校,在那个读书是一种奢侈的年代,家里唯一读过书且表现优良的她被一眼看中,成了民办教师,与其他两名教师一起,成了乡里渴望知识的孩子的救命稻草。这时的他,也早已大学毕业,来到了与她隔了两座大山的高中教政治。
三十岁,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这时最小的孩子也已咿咿学语。在学校的丈夫十几天才能翻过两座大山回家一趟,于是,单薄的她撑死了半片天。她知道每一天凌晨五点钟天空的样子,那是被厚布遮住般的灰黑,透出几缕微弱的光芒。于是,她揣着这微弱光芒望向山的那头,想着他信中的字字句句,眼中笑意朦胧,仿佛那期望目光已穿透那山川河流。就这样,她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劈柴,煮汤,服侍公婆,安顿好四个孩子后她拿上了头天晚上熬夜备好的课去了学校。中午,她哑着嗓子,拖着一身疲惫尽可能快的往离学校半小时路程的家里走。沿路是她最喜欢的雏菊在阳光下摇晃着金黄的小脑袋,可她已顾不得去俯下身,好好欣赏这平淡日子里的鲜活。推开门,四个孩子扑过来抱住她的腿,什么也不说,只是用那一双双如湖面漾起轻微涟漪般透亮的双眸望向她。这一刻,她满是心疼,溢出眼眶的不止是眼泪。
于是,她把属于她的那些少的可怜的汤也分给了孩子们。她听见了肚子里的咕咕做响,默不作声,坐在那院子明媚处,一针一针的纳着鞋垫,她想着要趁中午闲工夫多纳一些,好让丈夫翻过那两座大山回家时舒服些,眼中星光点点。
四十三岁的六月。孩子们都已长得出落,比她还高出许多,去了丈夫的高中念书。她把公婆托付给哥嫂,将自己关在了房中,谁也不见。她告诉孩子和丈夫,逢人问起自己就说是病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年底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从民办教师转正,才能和丈夫一样。这一年,她连娘家都没回过。于是,在那个大家都坐在树荫下乘凉的夏天,她独自坐在那个不透风的小屋里,写写记记。热到发昏时,就把脸闷进桌旁的水盆里,继续学。
那半年,本就瘦小的她又瘦了些许。没人知道在那些日子里,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从未提及那个六月里的崩溃难熬。转正那天,她终于依了丈夫,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她望向丈夫温润眼眸的那一刹那,脸上像是被雾气熏过般的银珠点点。
五十四岁,儿女们都成了家,她与丈夫也都退了休,两人工资慢慢涨了起来,于是,他们在县城买了最早的一批商品房。终于,白米大肉与各色蔬菜不再是过年专享的奢侈,可她却说,还是那时的白米饭更香更糯。
七十五岁。四世同堂,最大的孙女也像她和丈夫一样,成为了一名教师。她在老伴八十大寿那天,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看着一屋子的热闹笑的合不拢嘴。她双手扶在膝上,前后微微摇动着,望向老伴不再明亮的双眸,笑着说:“老陈,这一辈子啊,真好”
那天,她慢慢坐下阳台那把老竹椅,双手扶在膝盖上,斜阳拂过她的缕缕银丝,也拂过她面前台子上放着的雏菊,温暖地像是从太阳里绽放出的朵朵金花,熠熠生辉。
我望向奶奶脸上的斑驳迂回,恍惚间,视线竟有些模糊,晶莹剔透。
她说这人生几十年,仿佛不过一个秋,参透了所有。
484 |
0 |
1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