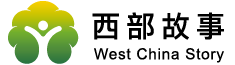那个小院里,住着一个老头,今年七十一了,寥寥无几的头发全是雪的颜色,腿脚不利索,眼睛也不好使,不听话睫毛总是往眼皮里面长,需要定期夹一下,为此,我未曾走远。
夹睫毛是个细致活,需要拿个小镊子,轻轻地从眼睛里面拔出来,这样就不会让眼球十分难受。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年开始的,但在我印象中,第一个做这个工作的是大姨的女儿,可后来她出去上大学了,就交给了我姐姐。姐姐每次总是让我边看边学,给我讲些要领,我想,她一定也快要远去了吧。果然,很快,她也去了别的城市上学。全家最小的我,终于也该接手这个位置了。
记得第一次让我夹,我十分不情愿。因为我害怕,怕我手一抖……外婆说,这老头子现在就指望你了。看着他被刺痛得难受,泛红的眼睛,在眼眶里的几颗泪好像快要落进我心里,我终于把那泪化为勇敢,拿起了那把镊子。从五年级到高二,一拿就是七年。这七年,我的手法越来越娴熟,从那双眼里读出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那是一双从四五十年代跨越到新世纪的眼睛。
那是一双让新世纪的宠儿探索四五十年代浮沉的眼睛。
那双眼里,是四五十年代人的责任与重量。
那时候他读了初中成绩不错,可迫于生计不能继续深造,只好早早毕业,在村里当会计,当主任,一当就从风华正茂当到四世同堂。外婆常跟我讲说:“改革开放的那几年,上面天天都是大大小小的事,他一下山开会,就是好多天不回来,回来了,也是忙着在村里挨家挨户跑。那时候刚生了你小姨,家里还有牛羊鸡狗猪,你妈和你大姨都还是小孩子,家里就我一个人,那简直是把人累垮的日子……”后来从山里搬下来,他的那些工作记录和那把算盘,一个不落的都带在身边。外婆时常说他:“就你把这些东西当个宝,当了几十年干部,工资比谁都低,还得不到一点好处,你自己的柴米油盐都搞不定还成天操心别人家的事。”读了点书那会儿,我也会常常感到不平,会发出疑问,但他从来都是用那双笑眯眯眼睛,就已经回答了一切。
那双眼里,是四五十年代人的质朴与踏实。
刚下山的那几年,他好像总是闲不住,天天往山里跑,弄些春笋,香椿,野菜野果子回来,分给院子里的邻居们。后来检查出风湿,也跑不动了,只好闲在家里。那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相依为命的几年。他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其中就有为什么大人要吓唬小孩子不听话就会被狼吃掉,因为那时候深山老林里是真的半夜会有狼来偷羊,可能某一天夜里,就出现在家门口对你目不转睛。我说“你一定是骗我的,哪有那么可怕啊。”他回答我:“你都没见过我的火枪,一打就把它们吓跑了。”可是我想,对待那些未知的威胁,谁能没点畏惧,可是在生存面前,也只得若无其事。
和现在的很多职业会有职业症一样,他也有。他很注重纪律。他会手把手教我系红领巾,给我讲革命时候的红色故事,要求我每天都必须洗干净,系规范。虽然在教完我珠算之后我的学习他也插不上手了,但是每学期开家长会,他总是很积极认真早早到学校,和那些年开会一样,拿上他的小本本记录老师说的话,回来一条一条的要求我,一定不可以违反班规校规,不可以攀比炫耀,必须认真努力,必须尊敬师长,必须善良。用他那双笑眯眯的睛,让我规规矩矩当学生。那些看似平常的小要求,也在不觉中为我的成长添上了浓墨重彩。
那双眼里,是四五十年代人的好奇。
退休以后的平淡日子,对于一生都在为生存而
硬撑的他们来说不是与诗书写作为伴,也不会有浪迹天涯的勇敢。他只是一言不发,用眼,用心,学会了对他来说是个新事物的“麻将”,自此多了个打发时间的东西。在我渐行渐远的路上,我把新时代手机带到他的旧世界,他也学会了打电话,听音乐,拍照片。生命已经进入倒数的他,仍然在用那双笑眯眯的眼睛,观望着这个世界。
这个清明假期,我同样的如期而至,你们同样的翘首以盼。 归家之时,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你们准备的舍不得吃的一定要等我回家才吃的佳肴,我才觉得那满田的油菜花格外金黄,路边的樱花极致粉嫩,车窗外吹来的风也温柔得刚刚好。
在我们不停追逐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的时候,他的日子再慢再平淡不过,而我,又一次用最独特的方式,从他的眼里,看到了跨越世纪的一天一天。我无法书写那些过去的时光,却能清醒的读出他们的饱经风霜。
又该坐上从边远小镇上去往县城的车上,书包里是你们塞满的鸡肉,土鸡蛋。我能透过窗看见前方等待我的微光,只是时间,好像又有些匆忙。
小院里的老爷子,别舍不得我,就当是我像小时候拽着你的袖口跟你撒娇一样吧,我就出去一会儿,你别担心,我不走远,我很快就会回来。
590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