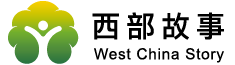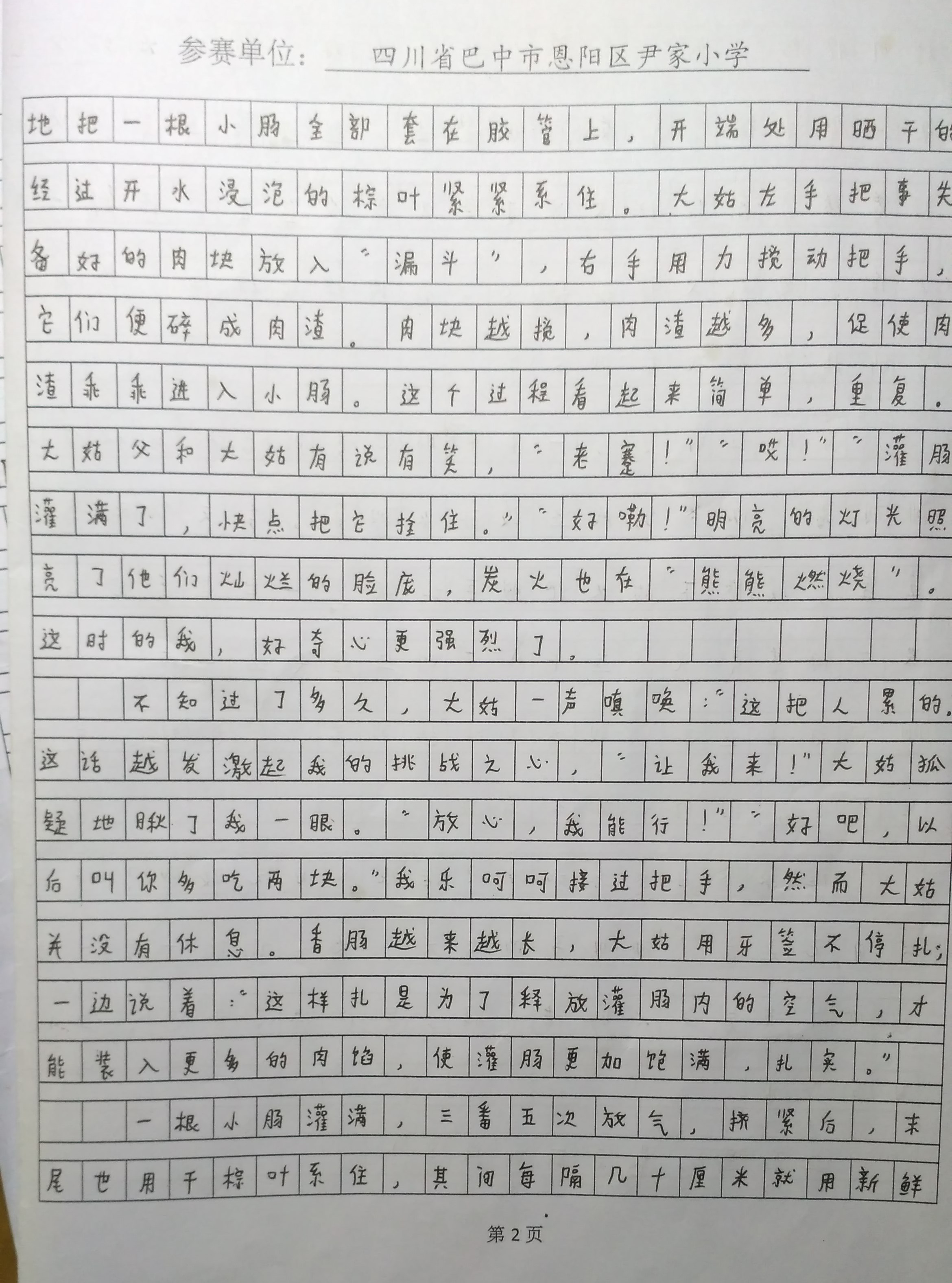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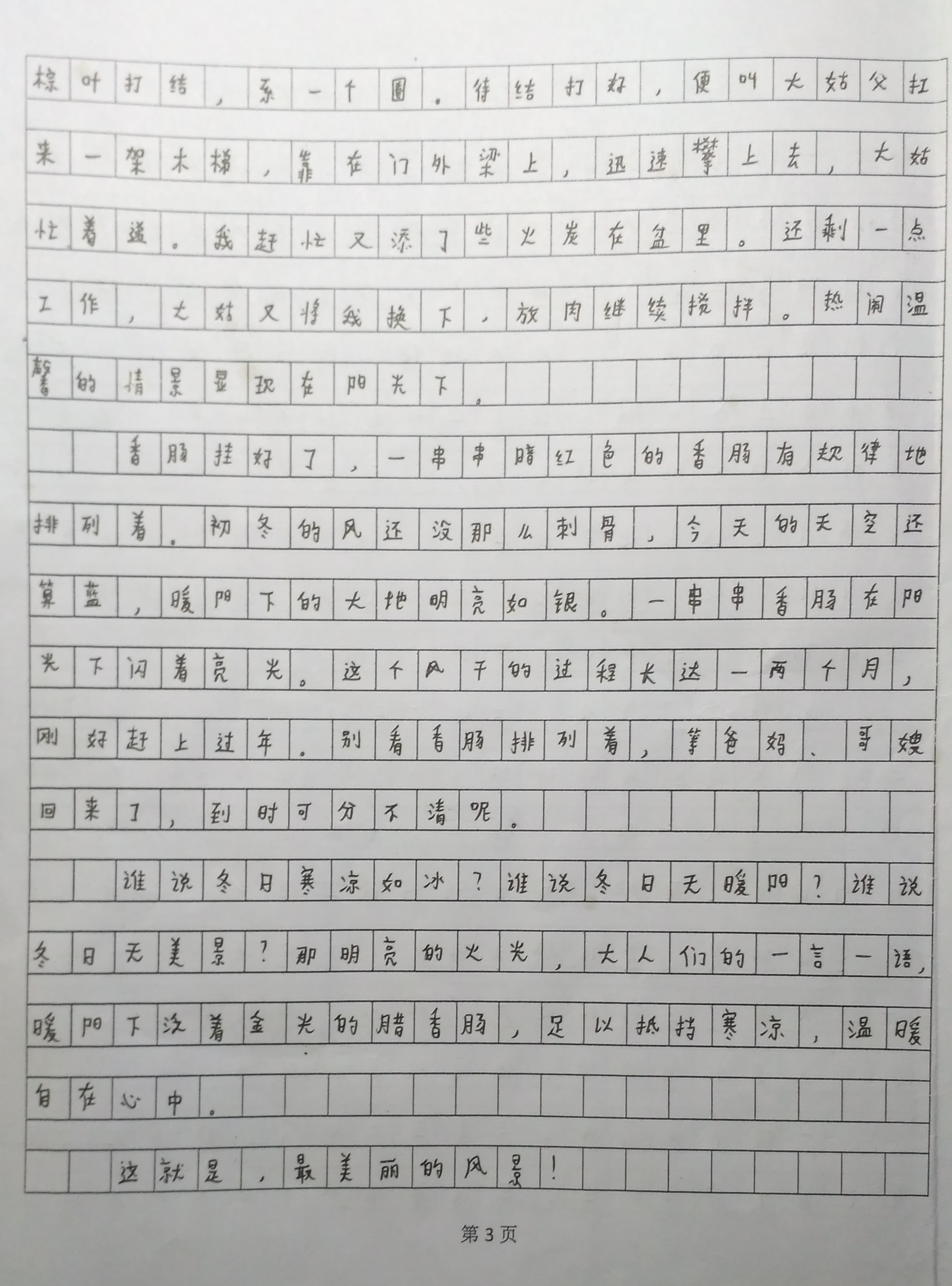
厨房里,橘色灯光下,案板上满是锅碗瓢盆。左边锅里装着猪血,右边盆里是猪大肠,中间盛着一大碗猪心……头上已有少许白发的大姑准备好新鲜的猪肉,绝大部分瘦肉,零星的肥肉。屋外鸡鸣、鸭叫此起彼伏。
大姑却丝毫不受纷扰。只见她迅速地上下飞舞着菜刀,菜板上的肉就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接着把它们一股脑儿倒进大铁锅里,撒入海椒粉、胡椒、新鲜的橘子皮、鸡精、白糖、花椒,倒入一整瓶白酒,再用力揉捏,搅匀,确保每一块鲜肉裹满佐料。
另一边,大姑父用热水把猪小肠浸泡半小时后刮干洗净,拿来做腊肠的"外衣"。
关键时刻--灌香肠,到来了。我家用的是机器。它小巧玲珑,整体呈暗红色,"主干"上面的小槽类似漏斗,是放肉的地方;左边有一小段胶管,右边是搅动的把手。只瞧见大姑父娴熟地把一根小肠全部套在胶管上,开端处用晒干的,经过开水浸泡的棕叶紧紧系住。大姑左手把事先备好的肉块放入"漏斗",右手用力搅动把手,它们便碎成肉渣。肉块越搅,肉渣越多,促使肉渣乖乖进入小肠。这个过程看起来简单,重复。大姑父和大姑有说有笑,"老蹇!"哎!"灌肠灌满了,快点把它拴住。"好嘞!"明亮的灯光照亮了他们灿烂的脸庞,炭火也在"熊熊燃烧"。这时的我,好奇心更强烈了。
不知过了多久,大姑一声嗔唤:"这把人累的。"这话越发激起我的挑战之心,"让我来!"大姑狐疑地瞅了我一眼。"放心,我能行!"好吧,以后叫你多吃两块。"我乐呵呵接过把手,然而大姑并没有休息。香肠越来越长,大姑用牙签不停扎,一边说着:"这样扎是为了释放灌肠内的空气,才能装入更多的肉馅,使灌肠更加饱满,扎实。"
一根小肠灌满,三番五次放气,挤紧后,末尾也用干棕叶系住,其间每隔几十厘米就用新鲜棕叶打结,系一个圈。待结打好,便叫大姑父扛了一架木梯,靠在门外梁上,迅速攀上去,大姑忙着递。我赶忙又添了些火炭在盆里。还剩一点工作,大姑又将我换下,放肉继续搅拌。热闹温馨的情景显现在阳光下。
香肠挂好了,一串串暗红色的香肠有规律的排列着。初冬的风还没那么刺骨,今天的天空还算蓝,暖阳下的大地明亮如银。一串串香肠在阳光下闪着亮光。这个风干的过程长达一两个月,刚好赶上过年。别看香肠排列着,等爸妈、哥嫂回来了,到时可分不清呢。
谁说冬日寒凉如冰?谁说冬日无暖阳?谁说冬日无美景?那明亮的火光,大人们的一言一语,暖阳下泛着金光的腊香肠,足以抵挡寒凉,温暖自在心中。
这就是,最美丽的风景!
679 |
0 |
0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