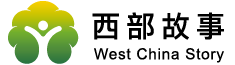一深一浅的脚印印成了黄土高原最凝重的记忆,白衣素麻迟缓地在黄土高原上行走,铜锣唢呐随着黄椭纸钱游走在黄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齐腰高的麦子被践踏倒在地上,踩踏成烂泥散发出一股青幽幽的味道,生死这条道上来的人来了,走的人也就这样走了。
我与母亲走在街上,冷风透过秋裤刺在腿上竟有些干烈,母亲突然停在一条窄巷面前带着浓烈的西北腔指名要的东西:棉衣,棉裤,宝蓝色棉袄,黑色棉帽,贴身内衣,黑色棉袜,还有棉鞋,买棉的是为了让奶奶去世界的另一端能够穿暖不受冻。老头一件件的取出来给母亲过目装进黑色塑料袋里,实则奶奶二十多年前就为自己做好了寿衣,秋天收麦子担到集市上去买,冬天则盘在炕上为自己做寿衣,恰逢今年雨水格外的多,寿衣早已捂得发霉,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为自己做寿衣是何等感觉?
母亲和临家的婶婶将买来的寿衣一件一件,一层一层的为奶奶穿上"身子昨天擦洗干净着哩——人活着的时候没为自己活两天,现在好了无牵无挂的就让妈去那边好好活两天。"母亲眼里没有泪,异常的平静。奶奶的两个女儿,我的两个姑姑,被村上请来帮忙的人拉到旁边的屋子里,邻家婶婶扶着姑姑的背"人走的时候千万别哭出声来呀,让老婶子安心走呢,万一听见你哭哩,有的放心不下……"
院子中间是一个木炭火盆,炭火在静静的燃烧,无烟无焰,烧过后留下一层白色的碳灰,仍然明晰地显露着木炭本来的纹路,看得见星火却感受不到温暖。老院子里挤满了人,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帮忙,平日里豪放的女人们正蹲在地上温柔利落的洗菜,奶奶安详的躺在堂屋里嘴里含着几枚硬币,古人认为,冥河上有船,也就必有专门负责摆渡的舟子,亡灵渡河,当然也应该象人间一样,付钱给舟子,否则很可能受到舟子的责难,甚至无法渡河,又回来找子孙的麻烦,亡灵口含的钱就是付给冥河舟子的船费,也希望老人来世能够幸福美满,供台上放着一碗用奶奶秋天捂得麦子做的甜胚子,面条,奶奶生前就爱吃自己种的麦子,到最后也没变过。
麦子的一生又何尝不像人。夫妻,父子,父女,母女,子孙一场,情再深,义在厚也是电光石火,青麦叶上的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的心中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孤儿,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儿女的感恩,老伴的思念,她已惘然,我们只好相信:蜡烛燃烧完了,烛光仍在;-麦子收割完了,价值仍在。在人生旅程的最后一页,老人的子女要为老人献上最后的孝心,姑姑买来羊,大家围着跪在一起,另家的老者将提前准备好的水,酒,石灰洒在羊的身上说一些宽慰的话进行祷告,若羊利利索索抖动身体则就说亡灵收到了这些孝心,这就是我们西北丧事中的"领羊"。奶奶领羊那日,我们子子孙孙披麻戴孝,仿佛奶奶的灵魂真的附在了羊的身上,一双双湿润的眼睛温柔的凝视着那只羊,是希望,是想念,是爱……
父母亲请来的阴阳先生(为亡灵悼念的人),邻家老人也在为亡灵悼念,嘴里念着我们听不懂的字符,但是这个乐调早已让所有人泣不成声,老人们说,念经文是对亡灵最好的祷告与超度。奶奶的尸骨在家里待了三天,祖祖辈辈一直遵从"入土为安","落叶归根"。在我们西北兰州,老人的棺材是要青年人抬得,因为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山路,棺材出门时阴阳先生会说一些避讳的生肖,这些生肖的人是不能送棺材上路的,否则来年会有不顺,虽说是很迷信但是祖祖辈辈还是一直遵从着,传承着这些习俗,亘古不变。老家信奉棺材头要大儿子抬的,身为家中的长子到最后要担起家中的大梁,父亲埋着头抬着沉重的棺材,我发现这个在我眼里高大威猛的男人忽然间变得那么矮小了,腰板没有以前直了,头发也没以前黑了,我无意中看见父亲偷偷摸了把眼泪,这个从来没有低过头的男人终于哭了。棺材出门了,天空中微微飘起雨丝,湿润的空气混着泥土的气息,麦子熟了。阴阳先生开始上路了,父亲抬着棺材头,我扶着母亲,最后唢呐破空而出,他穿行在寒风里,黄土中。邻居街坊在各自家门口点上火送亡灵,浓烟笼罩着的村庄仍有火星明明灭灭,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黄土高原的田埂上金灿灿的麦子一片片的倒下,换做往日这些人里定有奶奶的身影的。泥埂上有人在奔跑,怀里抱着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泥埂与大路的接口是,点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哥哥(长孙)在路口对那个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男人深深一拜,每个路口都响起沉闷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夹杂着"咚,咚"的鼓声,黑与白交织在一起,时而传出几声哀嚎,此起彼伏,竟像是一种低暝。麦子散发而出诱人的味道,埋葬在黄土高原的每一寸黄土中,你培育了它们一生,它们陪你入了半世,棺材留在了黄土高原,我再也不用担心你会孤单……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麦子熟了。
910 |
0 |
1
总数:0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