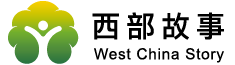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陈小姐:您醒了?" 听到陈静的呻吟,穿粉色护士服的护士走了过来。陈静强挤出了一个微笑,在右手边的电脑上按:"是啊,好多了。"
自从上次火灾,陈静就住进了这家医院——脑损伤和皮肤大面积烧伤。一位最好的大夫主治。
"对了,陈小姐,我们还是没能找到您的父亲,很抱歉。"
她一愣,微微点了点头,只见一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淌下。
"再来一点吗啡?很痛吧。"
于是她又陷入了沉睡中。
她是个孤儿,小时候家里没钱再养活子女,父母迫不得已将她送了人。听养父母说,她的父亲身材高大结实,是个搞医学的,其余的就不知道了。
自从住进医院,她就被查出了肺癌晚期。她感到绝望,她想在旷野里嘶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甚至想寻短见,想在吗啡的麻痹中解脱。
主治医生倒不错。几周以来她其实醒来过几次,想说话却没有力气。她竭力的睁开双眼——尽管也只是眯着缝——看见他在闲暇之余来到这个病房,与护士吩咐些什么就匆匆离去。有一次夜里好还看到了他拿着微光手电筒来到这儿,仔细打量着自己的资料,盯了许久,嘟囔了几句就转身走了。
窗外,树上稀稀两两悬着几簇摇摇欲坠的火焰。鸟儿开始飞向南国,远远地地只能望见成群的斑点排着行阵盘旋移动——时候不早了。
一日清晨,主治医生又进了这病房。看到陈静睁开的双眼,他欢快地轻声说:"你醒啦。"
"大夫,我还能活多久?" 陈静终于睁开了眼,盯着大夫。
"怎么了?"
"你知道的,我有肺癌。"
他瞥了一眼陈静,停下手中的笔,轻蔑地,甚至是从鼻孔里发出声音:"呵,你想怎么做?"
她没有回答,望向窗外的斑点们。
"我找到你的父亲了。"
突然,陈静感到周围的一切动静都暂停住,没有声音,只有医生的嘴在动。
她不顾身体的剧痛翻过身,大喊;"他在哪儿!"
"别急,他在哪儿我还没调查出来,不过…"
"不过什么"。
"有一个人跟你的DNA匹配。"他说得一字一顿。
陈静觉得心头的阴霾顿时敞开了,阳光钻了进来,暖烘烘的。 没等陈静追问,他就走了。
当天夜晚,她一直在想:为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父亲",她一定——一定要活下去。
时间就像白驹过隙,一晃就到了深冬。雪堆满了枝头,仿佛随时要塌下来。窗外的一切就像一张被肆意泼上白漆画板,到处洁白一片,分不清了东南西北。
陈静和那位医生的相处融洽。他讲了许多爸爸的事,知道陈静爱吃芒果,知道陈静小腹部有一小块胎记。有时候陈静真希望他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个人,想如同孩子骑在他宽大的肩膀上。
那天,陈静被悉悉率率的声响吵醒——事医生和护士们在交代病情。刚想打招呼,她被一张露在医生口袋外的纸吓得怔了神,笑容凝固在脸上。 那纸上写:陈书华与陈静的DNA相似度为百分之九十九。
陈书华?是谁?快想想……好像是自己的主治医生!还是谁?这个名字怎么异常熟悉!就在嘴边了……怎么说不出来!脑袋好像快要炸开!对!养父母提起过这个名字!是爸爸!
她欣喜若狂,又异常平静。她想跳下来拥抱他,去听他的心跳:又想趴在床上,捂着被子大哭一场。
医生将护士打发走,看到呆滞的陈静,微笑像一朵大丽菊般绽放。
"好点儿了?"
"不,不好。"
"我为你做一个全身检查。"说着,他弯下腰,去为陈静安装装置。
就在那时,陈静贴近他,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紧紧抱住了他。
几个星期过去了,爸爸没再回来。正当陈静翘首以待时,一封信由护士递了过来。她轻声念了起来。
"亲爱的陈静;
当你看到它时,我们就正;好一个月没见了。对不起,请原谅我这个撒谎者,我骗了你。我不是你的父亲,老陈在零三年抗非典时参与救治工作,再回来时,只是一枚荣誉勋章了。他在得知自己被传染后告诉我,他曾有个女儿,叫陈静。你的名字让我想了他的话。在我想象到这种可能后,我发现你灰心丧气,闷闷不乐,就因为被疾病击垮了。没错,夜里探望,让你看见报告单,说明我找到了你父亲等等,都是我计划好的。这我别无选择,请原谅。
癌症怎么了?你应该不会想到我也是肺癌。但我在用我生命的最后时光做我想做的事,做我该做的事,这就够了。 不要找我,
好了,时间不早了。早安。"
她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打湿了信纸。
鸟儿开始北归了。树梢上的积雪融化,慢慢汇到了一起滴下去。阳光蔓延了进来,为这里带来光明和希望。窗外树梢上冒着绿油油的新芽,它顶着薄雪,终于钻了出来,在光芒下脉络分明。
"陈小姐,怎么了?又开始痛了吗?需不需要吗啡?"
"不,不用了。我要离开。"
护士惊恐地望着她。"您要去哪儿?"
"你先猜猜。"
正当护士瞪大眼睛,吸气要说出那恐怖的字眼时,陈静释然一笑:
"不,你猜错了。"
600 |
4 |
2
-
评论者:樊秉源
评论日期: 2018-04-07
-
评论者:李戈
评论日期: 2018-04-03
-
评论者:樊秉源
评论日期: 2018-03-24
-
评论者:樊秉源
评论日期: 2018-03-24
总数:4 当前在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