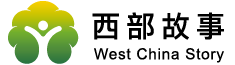那一次,我在与同学们跳皮筋时摔伤了脸,妈妈接到学校的电话后立即赶到学校,用飞一般的速度将正在嚎啕大哭的我送到卫生所,经过医生的包扎,我有了笑脸,妈妈这才输舒了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妈妈是一位“超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妈妈总能化险为夷。

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六年级,我开始变得叛逆。妈妈的每一次叮咛我都觉得是废话、是唠叨,她的许多次关心都被我拒之门外,她的“唠叨”被我屡次顶撞,妈妈的真心亦被我多次伤害。

那一次,期中考试没有搞好复习的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张满是红叉的考卷,我拿着试卷走进家门,妈妈一直追问我的成绩,我将试卷摔在了他的面前,要她看个够,妈妈看到了我的成绩,开始责问我,对我进行一番又一番的教育。

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拿起自己的试卷,气冲冲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上来,我便“啪”的一声关上了门,妈妈被锁在了门外。那一夜,我听见母亲哭了,我心中的“超人”流泪了。

那一次,我在与同学们跳皮筋时摔伤了脸,妈妈接到学校的电话后立即赶到学校,用飞一般的速度将正在嚎啕大哭的我送到卫生所,经过医生的包扎,我有了笑脸,妈妈这才输舒了一口气。那一刻,我觉得妈妈是一位“超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妈妈总能化险为夷。

十二岁那年,我上了六年级,我开始变得叛逆。妈妈的每一次叮咛我都觉得是废话、是唠叨,她的许多次关心都被我拒之门外,她的“唠叨”被我屡次顶撞,妈妈的真心亦被我多次伤害。

那一次,期中考试没有搞好复习的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张满是红叉的考卷,我拿着试卷走进家门,妈妈一直追问我的成绩,我将试卷摔在了他的面前,要她看个够,妈妈看到了我的成绩,开始责问我,对我进行一番又一番的教育。

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拿起自己的试卷,气冲冲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妈妈跟了上来,我便“啪”的一声关上了门,妈妈被锁在了门外。那一夜,我听见母亲哭了,我心中的“超人”流泪了。